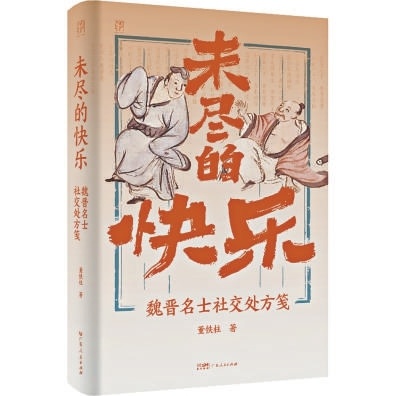
提到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群体的黄金时期,很多人都会联想到魏晋,那是一个士人可以尽情挥洒天性、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的时代。鲁迅、冯友兰、汤用彤等一众大家都不吝笔墨去描摹勾勒出魏晋士人们有趣的灵魂,关于“竹林七贤”如何谈玄论道的故事更是被反复谈起,因为他们率性而为、自由洒脱的生活方式,拥有着穿越时空的魅力。
这一切,最早都被南朝皇族刘义庆搜罗在了他的《世说新语》一书中,《世说新语》主要讲的是魏晋士人的生活趣事,其中也包含了一些以士族身份问鼎皇权的政治家,但是这并不妨碍《世说新语》内容的可读性。《世说新语》简直可以说是魏晋时期士人生活的八卦合集。在这里,一贯正襟危坐的道学先生也有被几句玩笑话弄得狼狈不堪的时刻,振作激情去指点江山的名流雅士,也会因与妻子的拌嘴或见证晚辈的青出于蓝而汗流浃背。那些不平凡的“事业型强者”的精神世界中,因此充满了各种平凡的快乐。
董铁柱的新著《未尽的快乐》,正是由“快乐”这一主题入手,打乱重组《世说新语》原有的篇幅结构,对魏晋士人的精神史作出全新的阐释。在他看来,魏晋士人快乐的源泉,并非是因为当时人对于“礼乐名教”等条条框框的刻意颠覆,而是仍基于他们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。马克思曾有一句名言——“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集合”,即使潇洒如魏晋士人,也需要面对《礼记》中记载的君臣、父子、长幼、朋友、同僚(宾客)、兄弟和夫妻七种基本的人际关系,并从这些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定义自我。但是,这些社会关系对于他们而言并非是束缚,恰恰相反,正是这些关系的存在成就了士人群体丰富多彩的人生。
例如,经过董铁柱先生的重新解读,对女儿过度苛刻,借给她一些结婚用的钱后就要匆忙索回,简直一毛不拔的大士族王戎,其实是想通过这种看似极端的方式教导子女独立生活的重要性;在北方陷入战乱后拥护司马睿再造晋室、人称“江左管夷吾”的琅琊郡士人王导,也会因为在闲暇之余的棋类博弈中与儿子围绕该不该“悔棋”产生争执,全无政治家的风度;即便是视财如命、怎么看都不像文化爱好者的石崇,也会因为好友王敦不理解自己对儒家理想的高远追求而抱怨连连。这些关系中,有基于血缘的父子(女),也有后天形成的朋友关系。这些多样的社会关系推动着魏晋士人展现出了他们鲜为人知、却再正常不过的性格另面,而这种真性情的流露,不仅没有冲淡他们的历史影响,反而让人物形象更加鲜活。
《未尽的快乐》一书,其实想说明一个看似很简单的道理,无论是谁,无论在哪个时代,人们都会去追求快乐,但是本书所指的“快乐”并非简单生理意义上的捧腹大笑,用作者的话说,这是一种“内在而自足的精神世界”,不以任何外界因素为转移。例如陈婴的母亲在秦末天下大乱、群雄并起时并不鼓励儿子去谋取功名利禄,而是看到了政治野心的膨胀也会对那些普通人的生活造成反噬,她洞悉了追逐人间富贵的代价之高,因此更希望儿子能够平安地过完一生。陈婴与母亲对平淡生活的坚守,使其因远离政治漩涡和战乱,最终顺利出仕新朝,这未尝不是一种快乐。曹操与袁绍年轻时并非如同后来官渡战场上要拼个你死我活的政敌,而是相谈甚欢的挚友。曹操甚至通过捉弄袁绍来寻找快乐,这显然与后世对曹操心狠手辣的枭雄印象存在很大的出入。按照董铁柱先生的观点,刘义庆把这个故事记录到《世说新语》中正是在提醒读者,没有人会拒绝寻找快乐,而在和袁绍被人追赶时,曹操虽然嘲笑陷入草丛中的他,还故意大声呼喊来刺激手忙脚乱的袁绍,但曹操并未真正撇下袁绍独自逃走,这也反映出曹操从朋友关系中找到了快乐;出身名门的王述在与儿子王坦之交谈时,不在意王坦之已身为人父的身份,仍将其当作孩童一样捧于怀中交谈,也反映出魏晋士人从亲情中所获得的快乐并不以时间或年龄为转移;在淝水之战中运筹帷幄,大破前秦数十万大军的谢安,也会因为疼爱兄弟、不忍看其犯错乃至于丢失性命而自降身份,主动为他分担来自下属质疑等压力。谢安从兄弟之情中收获了快乐,但这与其身份尊卑却并没有直接关系。因此,在那个读书人要按照“九品中正制”被分出高下优劣、朝廷在选官用人方面排斥寒族的门阀时代,时人对于快乐的感知却并无等级之分,这也成为士人少有的心灵慰藉。
当然,在作者的笔下,魏晋士人的快乐并非都是纯粹的,有时候也会因社会环境的复杂而表现为“苦中作乐”。如曹魏统治被司马氏架空后,士人群体连遭打压,已噤若寒蝉,而身为“竹林七贤”之首的阮籍则当着司马昭的面旁若无人地放声高歌,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。阮籍并非不清楚司马昭政治手腕的狠辣,但仍采取了这样一种极端的方式捍卫个体的尊严,也让司马昭得以顺势掩饰个人野心,但是当涉及对下一代的教育时,以“简傲”闻名的阮籍却告诫儿子应该低调处世,不要以自己为榜样。对于阮籍而言,快乐只是表象,是其苦闷心理的某种外延,但二者却要在他身上实现自洽,于是便有了“苦中作乐”。
其实,魏晋士人之所以能够留下如此多的关于快乐的故事供后人去品评,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当时皇权衰微、士族轮流掌权,名门望族以庄园财富和几近世袭的权力为后盾,如此才能心无旁骛地沿着与自己有关的各种社会关系去寻找更纯粹、更真实的快乐。至于处在少数民族南下与地方军阀混战夹缝中的底层民众,他们却鲜有精力去感知快乐,更不会留下多少与“快乐”有关的详细记载,看看魏晋以降此起彼伏的流民起义便可知晓。而到了《世说新语》一书作者刘义庆所处的时代,士族虽然仍保留着一定财富与声望,但军政大权已经基本转移到了依靠军功起家的寒门手中。刘义庆对于魏晋时期名人生活趣事的搜集,更像是在纪念一个已经回不去的时代,魏晋士人的那种随性之乐,在南朝似乎也已成为奢侈品。不过作者认为:《世说新语》中所记载的那些魏晋士人享受着“未尽的快乐”,或许也在无意中点出了《世说新语》绝非古人“快乐史”的绝唱。因为人类精神的欢愉从不会消失,只会转移。唐朝以后兴起的传奇、小说和话本,哪个没有承载人世间的快乐?只是这种快乐已经不再拘泥于《世说新语》中记载的“精英圈子”,而是飞入寻常百姓家了。
来源:北京晚报
作者: 李文畅


